槟榔,一名宾门、仁频、洗瘴丹、螺果。陶隐居曰:“尖长大而有紫纹者曰槟,圆而矮者曰榔。出交州者,小而味甘;出广州者,大而味涩。”槟榔在六朝时就为人们崇尚,《南史》有“刘穆之以金盘盛槟榔,宴妻兄弟”之记述。
槟榔为棕榈科槟榔属植物槟榔的种子。《南方草木状》载:“槟榔树高十余丈,皮似青铜,节如斑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稠直亭亭,千万若一。深秀无柯,端顶有叶,叶似甘蕉,条泒开破。仰望如插丛蕉于竹桫;风至独动,似举羽扇之扫天。叶下系数房,房缀数十实,实大如桃李,天生棘重累其下,所以御卫其实也。味苦涩,剖其皮,煮其肤,坚如干枣,作鸡心状,破皮作锦纹者佳。”《晋·俞益期与韩康伯书》亦曰:“惟槟榔树最南游之可观,既非常木,且亦特异。余在交州时,度之,大者三围,高者九丈余。叶聚树端,房栖叶下,花秀房中,子结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缀实似谷,其皮似桐而厚,其节似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劲,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缒绳。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倾,下不斜,稠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则寥郎,庇其荫则萧条,信可以长吟,可以远想矣。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必当遐树海南,辽海万里,弗遇长者之目,自令人深恨。”生动地描述了槟榔的植物形态。
《名医别录》谓:“槟榔生南海,气味苦辛温涩、无毒,消谷逐水除痰辟,杀三虫,伏尸,寸白。”中医临床上常用以治痢疾、绦虫病、胆道蛔虫、血吸虫病等。用槟榔制成溶液点眼,可治疗青光眼。五代医学家和文学家,对槟榔的药用价值推崇备至。宋·黄庭坚曾托人几觅槟榔:“蛮煤雨里红干树,逐水排痰肘后方,莫笑忍饥穷县令,烦君一斛寄槟榔”。宋·朱熹也赞其治疾杀虫之功。诗曰:“忆昔南游日,初尝面发红。药囊知有用,茗碗讵能同。蠲疾收殊效,修真录异功。三彭如不避,糜烂七非中。”
粤人有咀嚼槟榔的习惯,常杂以砂仁、豆蔻,贮荷包中,竟日细嚼,唇摇齿转,吐汁鲜红。邱浚赠五羊太守诗云:“阶下腥臊堆蚬子,口中脓血吐槟榔。”渔洋山人调程给事早朝诗曰:“趋朝问夜未渠央,听鼓应官有底忙。行到前门门未启,轿中端坐吃槟榔。”程为海南人,故有此嗜好。朱熹也有《槟榔七绝五首戏简及之主簿》,其一曰“锦文缕切劝加餐,蜃炭扶留共一盘。食罢有时求不得,英雄邂逅亦饥寒”。梁·庾肩吾《槟榔启》曰:“无劳朱实,兼荔枝之五滋,能发红颜,类芙蓉之十酒。”
南方人咀嚼槟榔的风气,由来已久。之所以嗜嚼,是槟榔的功效使然。罗大经《鹤林玉露》载:“岭南人以槟榔代茶御瘴,其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盖食之久则熏然颊赤若饮酒然;二曰醉能使之醒,盖酒后嚼之,则宽气下痰,余醒顿解;三曰饥能使之饱;四曰饱能使之饥。盖空腹食之,则充然气盛如饱;饱后食之则快然易消。又且赋性疏通而不泄气,禀味严正而更有余甘,有是德故有是功也。”
历代诗人吟咏槟榔的诗句甚多,如:唐·李白的“何如黄金盘,一斛荐槟榔”。宋·唐庚的“织贝流肌滑,槟榔入颊红”。元·张翥的“槟榔新善啖,一斛宿醒空”。宋·苏轼的、“不用长愁挂月村,槟榔生子竹生孙”。
槟榔不仅是药物,也是海南岛黎族、苗族自治州民间喜庆之礼物。每逢喜庆节日,相互赠送,尤以婚期吉庆,不给喜糖尚可以,不送槟榔就是失礼。接待客人,总以槟榔招待:一片新鲜槟榔,一片木香树叶,再抹上贝壳浆糊,请您放在口中细嚼,以示盛意。
最近有资料介绍,常吃槟榔可促使口腔癌增加。据化验,槟榔中含有的石灰和老藤中含的黄樟素具有高致癌作用,故槟榔不可常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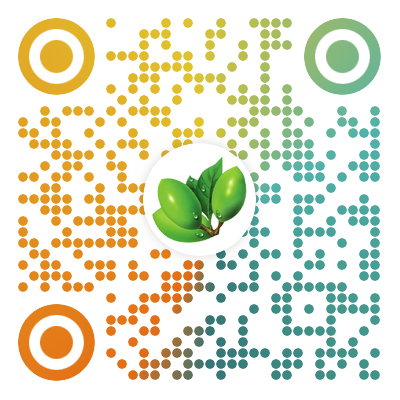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