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高的树上结槟榔,谁先爬上谁先尝,谁先爬上我替谁先装,少年郎采槟榔,姐姐提篮抬头望,低头又想,他又美他又壮,谁人比他强,赶忙来叫声我的郎呀……”
1930年,正当毛泽东率领着刚刚统一了番号与编制的工农红军面对第一次大围剿上演了一场“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的战争风暴时,这曲简洁明快的《采槟榔》首次经由一代歌后周璇的莺声燕语所演绎,正以黑云压城之势风靡着灯红酒绿的上海滩,在演艺圈子演绎了另一场“不周山下红旗乱”的流行风暴。有趣的是,《采槟榔》的作者——也便是名曲《夜来香》的作者——黎锦光,与毛泽东同为湖南湘潭人。民国九年,14岁的小黎锦光在第一师范补习班学习,班主任便是日后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受大街小巷广告的影响,世人大多知道毛主席爱吃长沙“火宫殿臭豆腐”,却未必了解这位开国领袖与黎锦光同为槟榔的忠实粉丝——事实上,湘潭人向来以爱吃槟榔闻名,对槟榔的喜欢不仅仅催生出了源于湖南民歌“双川调”的名曲《采槟榔》,也引出了毛主席的一段轶事——1952年冬,毛泽东的老师毛宇居带了些土特产进京请毛主席为学校题字,毛泽东一见槟榔格外高兴拿起就吃,一边吃一边还对劝阻的保健医生说起了湖南土话:“过去呷了几十年,从没检验过,冒得关系,冒得关系!”

惊艳了民国的周璇
湘潭槟榔:沐浴战火之后
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槟榔的原产地在东南亚,这使得槟榔这个名字对很多大陆人来说都有着浓浓的热带风情;然而槟榔最早进入大陆的视角,却是以湘潭为起点的。关于湘潭槟榔的传说最早能延伸至明末清初——据《湘潭市志》记载:顺治六年正月“湘潭屠城”之后,湘潭城一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一位安徽商人得一老和尚嚼槟榔避疫之法收尸净域,使嚼槟榔的习惯扎下了根;乾隆四十四年湘潭大疫,居民多患臌胀病,县令白景将药用槟榔分患者嚼之最终治愈了臌胀病,从此嚼槟榔的习俗便在湘潭正式流传开来。
如今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已经将槟榔咀嚼物与砒霜、甲醛一道列入“一类致癌物名单”,然而槟榔却早已以中医“四大南药”的地位融入了湘潭人的文化:一些地方花古戏和婚庆之喜等民间包事都无不有槟榔的赞语,比如《潭州竹枝词》写道:“风流妙剧话情杨,艳姿娇容雅擅长;一串珠喉歌宛转,有人台下掷槟榔”;大街小巷则更不乏相应的民谣民谚——
“槟榔越嚼越有劲,这口出来那口进,交朋结友打园台,避瘟开胃解油性。”
“龙牌酱油灯芯糕,槟榔果子水上飘,十里荷塘百里香,砣砣妹子任你挑。”
“新娘槟榔两头翘,一口两口我不要,三口四口不为多,我要五子大登科。”
类似的民谣民谚本已不可胜数,又因为槟榔的形状酷似银锭,民间又将它视为财富的免征,各家各户“赞土地”闹新春的时候,主人送口槟榔,客人会很开心的回应一句“老板是个财帛星,拿锭元宝赏阳春”,像极了万圣夜“Trick or treating”的东方版本。
湘潭槟榔已经发展出了旅行业。
槟榔与湘潭饮食文化自是有着不解之缘,对于湘潭人来说,槟榔如同口香糖或香烟,逛街的时候,码字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嘴里嚼一块,消食又解馋。然而湘潭槟榔情虽深,却并非槟榔的产区,撑起湘潭槟榔大旗的是加工业,若要论其老家,还要将视线向南,再向南,一直跨越大陆,来到中国最大的两个岛屿——海南与台湾。
海南槟榔:生活中的情与诗
古代敬称贵客为“宾”、为“郎”,而槟榔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东南沿海各省居民迎宾敬客、的佳果,于是便有了“槟榔”的美誉。或许这只是后人虚构的美好传说,但“客至敬槟榔”却一直是海南黎族传统的风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槟榔自然少不了吃槟榔——在黎族人的婚姻、社交、祭祀、拜年等习俗中均少不了槟榔的身影,男女间更是把槟榔当成了定情信物,一首当地的情歌唱得分明:
“送口槟榔试哥心,一口槟榔一口香,二口槟榔暖心房,三口槟榔来做媒。”
古代中原婚配之事极重礼仪,将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六礼”的规矩定得极其繁琐细致,然而到了这天涯海角的“蛮荒”之地,甜蜜的爱情由略带苦涩的槟榔“代言”,倒也别有一番风情。
海南名菜“槟榔花鸡”。
黎族人爱槟榔爱到了“以槟榔为命”的地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神奇的药效。正如每一枚硬币都有两面,嚼后致癌的槟榔消食祛痰,善加利用还对治疗青光眼、眼压增高等症有奇效——不仅如此,鲜槟榔还有一种“饥能使人饱,饱可使人饥”的神奇功效,这既能让贫苦的百姓免受饥肠辘辘之苦,又能让富贵人家尽享大快朵颐之乐,从这也便不难理解黎族人对槟榔如此深厚的喜爱了。如今,“槟榔花鸡”号称“三亚第一名菜”,那鸡是槟榔树下养的鸡,花是槟榔树上开的花,这恐怕是世间最让人大快朵颐的“花与鸡的相遇”了。
湘潭槟榔源于清兵屠城的悲剧,而黎族淳朴的人们更用一个老套而温馨的传说赋予了槟榔脉脉温情。相传五指山下的黎寨里,一个叫佰廖的姑娘的母亲身患重病需要用五指山之巅的槟榔作药引才能治得好,于是能歌善舞的佰廖就开始唱了:
“我不爱谁家的富有,我不爱你们家的钱财,我只爱对爱情忠贞不二的贴心人。谁能把五指山之巅的槟榔果摘回来,治好母亲的病,谁就是我最亲爱的人。”
五指山高耸入云、四面绝壁,在求婚的小伙子都退避三舍的时候,一个叫阿果的后生挺身而出,风雨兼程,跋山涉水,搏毒蚊、拒蚂蝗、刺恶豹、杀巨蟒,终于采到了山顶的槟榔。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槟榔在传说也成了黎家人的定情信物,直到今天,万宁、陵水、三亚一带的农村在迎娶拜堂期间还会散发槟榔给前来道贺的亲友,用这种方式传承着一个亘古的甜蜜祝福。
海南槟榔树自有南国风味。
源于悠长厚重的历史,黎家的槟榔也会因为偶然的因素散见于汉人的诗文。生性豁达的贬居名人苏轼对“口含槟榔头插茉莉花”民族风情的喜爱自不用说,这“岭南佳果”槟榔倒是颇多雅句:
“火布垢尘须火浣,木绵温软当绵衣。桄榔面碜槟榔涩,海气常昏海日微。”——元稹。
“寂寂孤村竹映沙,槟榔迎客当煎茶。岭南二月无桃李,夹路松开黄玉花。”——陈与义。
“绿玉嚼来风味别,红潮登颊日华匀。心含湛露滋寒齿,色转丹脂已上唇。”——王佐。
因缘际会与文人相连,与湘潭的俗语到底不同。不过听说如今乱知槟榔水已经成了三亚的“顽疾”,有倒是颇有伤风雅了。
台湾槟榔:“西施”的红唇黑齿
从海南省会海口向东约一千公里,会遇到一座更大的岛屿,那便是中国槟榔的第二个故乡台湾;而当下大陆人对槟榔的别致印象,也恰恰与宝岛台湾相关,那便是一个“风情万种”的职业——“槟榔西施”。
客官,来点豆腐?
说到槟榔西施,就不得不提鲁迅笔下的“豆腐西施”。《故乡》里有一段描写杨二嫂的文字曾收入大陆的教科书:
“我孩子时候,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但这大约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却并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却了……”
读者自然能明白为什么杨二嫂的豆腐卖得这么好——东南沿海通常把非礼的行为叫做“吃豆腐”,而经过鲁迅妙笔一点,“西施”一词也有了微妙的内涵,“槟榔西施”之名的由来也正源于此。20世纪90年代末,一些槟榔经销商为招揽顾客,专门聘用年轻貌美的女孩子,穿着低胸衣与超短裙,未见媚态妩然一段风姿,看客在心醉神迷之间自然也便解开了钱囊。当然作为职业的销售人员,槟榔西施们调制包装槟榔的手法也非常娴熟:取出槟榔,用刀切头去尾,从专门的盒子里剜出少许白泥膏,平摊在槟榔叶以去除槟榔的刺激方可给顾客享用。只是后来,槟榔西施越穿越少,直到严冬也只是一抹文胸一勾短裙,甚至出现了色情交易——直到最后台湾当局也觉得“有辱斯文”,于是与槟榔西施们签订了“八不准”公约,里面明确规定“不穿丁字裤;不露三点;不露屁股;不做放荡姿势;不穿透明内衣、内裤”等具体行为,多多少少有些让人啼笑皆非,如若周璇有灵,面对槟榔的如此后续,却不知做何感想呢?
招揽生意的“槟榔西施”。
浓妆艳抹的“槟榔西施”现象背后或多或少有着女孩们求生的无奈,然而嚼槟榔的习俗在台湾却可谓历史悠久。乾隆年间台湾海防同知朱景英就曾在《海东札记》中记录当时台湾流行槟榔的盛况:
“晱槟榔者男女皆然,行卧不离口;啖之既久,唇齿皆黑,家日食不继,惟此不可缺也。解纷者彼此送槟榔辄和好,款客者亦以此为敬。”
由这段描述可以看出,对于台湾人来说,槟榔同样是象征友谊、亲情的吉祥之物,人们对槟榔的喜欢并没有因为一沟海峡的阻隔而不同,相比之下,台湾人对槟榔的热爱已经狂热到不在意“唇齿皆黑”的地步了——台湾人吃槟榔喜欢一边嚼一边把红红的汁吐出来,人们不计较这样子粗俗,反而给嗜食槟榔者起了一个“红唇族”的雅号,而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个少女偶像团体的名字就叫做“红唇族”。更有甚者,国民党曾经在一次“省市长”选举中忽然意识到“红唇族”的强大影响力,加急赶印了200万个槟榔盒子,上印“支持宋楚瑜”字样,从这也能看出槟榔在台湾人心中独特的文化印记了。
你发如雪,凄美的离别……
台湾槟榔的产量高于海南,而且工艺更加独特:采收槟榔后剥除果蒂和较老的部分而后切开,再将石灰与彰化荖叶搅匀卷起置于槟榔之中,与老藤、石灰、槟榔一起嚼食。这种混合物食之如同饮酒,其感觉恰如周杰伦《发如雪》中所唱:
“红尘醉,微醺的岁月,我用无悔,刻永世爱你的碑。”
结语
槟榔以独特的方式牵连着中国人的生活——它是传统到写入唐诗宋词,它又现代到让人对“西施”们的浮想联翩;它是平常到已经形成了极大的产业链,它又是少见到远远不能被称为日常水果。它在海南与台湾广泛种植,却又是个名副其实的 “舶来品”——直到今天,人们还能在地图上的某个角落惊喜地发现槟榔山、槟榔屿、槟榔岛等地名,毕竟那才是槟榔的老家啊!
对,那个地方,同时是榴莲的老家——马来西亚。只是不知那遥远的国度,会不会有有那么一个“姐姐”,一边等着心爱的人采槟榔,一边唱着那首流传了近百年的情歌——
“高高的树上结槟榔,谁先爬上谁先尝……”
槟榔屿,值得去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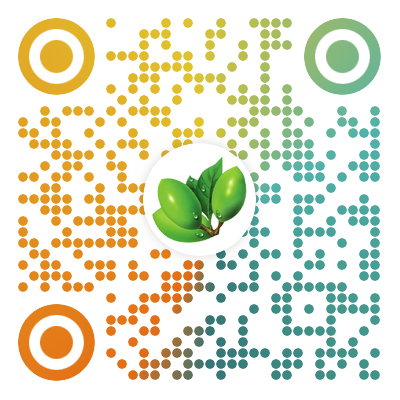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