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大气磅礴地流淌在三湘大地,当它临近湘潭时,迎头撞上一个绿岛—杨梅洲,杨梅洲过后便是窑湾。
窑湾依河而建,在这条1000余米的街道上有望衡亭、唐兴桥、潭宝公路长途汽车站等古迹。300多年前的一次大水退后,窑湾一带发生了瘟疫。正巧有一位来自海南,名叫南智的游僧在窑湾落脚,他的行囊中带有几斤伏毛果子(干槟榔很粗糙的一种)。那个年代的游僧都具备一些中药知识,知道槟榔具有杀虫、破积、下气、行水的功能,于是他将有限的伏毛果子分给百姓嚼食。有一天,一位做豆腐的师傅在接过他人给的伏毛果子时,不小心将它掉进了自己的卤水桶,转背他还是将那片东西捞起来塞进嘴里。谁知经过桶里的卤水除酸,伏毛果子里原先的涩味除去了一大半,味道好多了。从此湘潭人明白,点了卤水的槟榔,味道就是不一样。
一位有学问的世纪老人告诉我,这就是湘潭人嚼槟榔的来历。
看了这一段叙述,你也许会问,这么大的中国,难道这一切就只能发生在湘潭?其他地方就没有留下过海南游僧的脚印?其他的地方就没有豆腐坊?
在此,我想从另一个视角解释这个问题,切入点就是海南的三亚吧。世界不算小,但具备三亚那种“黄金海岸”五大要素的旅游景点,全球都屈指可数。这五大要素是:灿烂的阳光、澄碧的海水、洁白的沙滩、翠绿的树木和新鲜的空气。先决条件是这个地方必须是处于北纬18°附近。遗憾的是,世界上有些地方是处在北纬18°线附近,但或温度偏低或太干燥,并不是理想的“黄金海岸”。
纵观华夏大地,似乎早先只有湖南的湘潭凑齐了嚼槟榔的“五大要素”,首先,它必须是一个临江的、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小城镇。其次,在这个小城镇里有一群生活悠闲、衣食无忧的人。再其次,这个小城镇里的人喜欢吃“番椒”(“番”湘潭人读之为“ban”)即辣椒这种由域外传来的好东西,用以抵抗南方饮食的瘴疬;另外,他们还得特别喜欢吃烟熏的食物,如烟熏的鱼,烟熏的“土匪腊肉”。除以上三个要素之外,这个城镇的气候必须四季分明,冬天还得十分的阴冷、潮湿。由于家中无暖气,嘴里还需要嚼点东西来给自己升温,松弛一下冻僵的脸颊。最后,这个城里的人性情还得比较温和,对生活的要求不高,日常生活中磕磕碰碰出来的微烦小恼都能由口中一小片槟榔的一嚼一咽而烟消云散。与其他现象一样,当嚼食槟榔成为一种文化时,它也便有了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背景。
我将嚼食槟榔当作一种文化现象看待起源于10年前。一日,顺手翻开一张旧的《湘潭日报·雨湖》副刊时,发现竟有《嚼槟榔》专栏。罗夫猷赞槟榔的一首小诗使我对这个栏目刮目相看。对于湘潭人嚼槟榔,他是这样说的:“莫笑口中含把草,须知此物可提神。从来大快朵颐者,多是湘潭懂味人。”但有一日在《嚼槟榔》栏目读到的一则新闻使我大开眼界,从那一日起我对槟榔似乎有了新的认识。消息报道:在被押往刑场前,一名死刑犯向押解人员要一片槟榔,在通往刑场的路上,他一直在嚼着······
这是一个临死之人对人世最后的愿望!一个有灵有肉的人对生活最后的留恋就是一片小小的湘潭槟榔?如果一种习俗在某地扎根50年、100年,兴许你还可以说那种习俗尚未在该地先人的血脉中留下一点什么,但如果它在那一方土地上已生根了300多年,你能说那一群人的遗传中没有受到先人的影响?这也许是人类学家才能说清楚的事情。不过去我倒相信,习俗是可以遗传的。作家韩少功在讲到他当年下放汨罗时,见到了一种奇特现象:那里的成年男人最喜欢背手而行,甚至双手在身后扭结着高抬,高到可以摸肘的程度。那种别扭的行走姿态,普遍得让他十分奇怪。一个乡间老人告诉他:这是他们被捆绑惯了的缘故。这种现象在说,即使他们的先民身为战俘或奴隶的年代已很遥远,一种苦役犯的身份感已经进入了他们的遗传,使他们即使在轻松的时刻也总是不由自主地反手待缚。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这种遗传是始于黄巢、杨么、朱元璋、吴三桂给他们带来的一次次战乱,还是始于更早时代北方兵团的铁军南伐。这种男人的姿态,有人推定,是战败者必须接受的规范,或是战败者自发流露出来的恐慌和卑顺。
我引出学者的论断目的在于说明:咀嚼,咀嚼槟榔,对于湘潭人而言,也许已进入遗传学的范畴,无论是一个自由之身,或是一个双手被捆绑即将赴死的人,身体里的某种冲动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影响他的行为。
还是让我们的目光穿透历史的迷雾落在槟榔树的源头吧。
槟榔在海南种植已有悠久的历史,唐代文献曾记载:“槟榔长南国,产崖州乐会。”翻开古文字学,我们知道,我国古代“宾”与“郎”都是对嘉宾贵客的尊称,遇贵客临门,都要送上槟榔果表示对客人的尊敬和热忱。槟榔之名,即来源于此。其实,用槟榔作礼的风俗在海南岛上一直流传有一千多年了。岛上的地方县志上也有记载:“凡亲友来,先荐槟榔,宾主以此成礼,婚姻采纳,多用槟榔。”
除了把槟榔作礼外,在海南岛当地人还把它作为爱情的象征。很早以前,民间的订婚,就叫“送槟榔”。在情歌中也有用槟榔作为话题的:
隔河槟榔绿成荫,心想采摘怕水深;
掷个石子试深浅,送口槟榔试哥心。
一口槟榔嚼口香,二口槟榔暖心房,
三口槟榔来做媒,吃侬槟榔即侬郎。
如果有人认为嚼槟榔不能登大雅之堂,你则可以告诉他,他再雅也雅不过苏东坡吧。虽然诗人面对官场“不合时宜”,但他被贬至海南时,立刻与那里的风土人情融合到了一起,在海南也学会了嚼槟榔。“暗麝着人簪茉莉,红潮登颊醉槟榔。”有诗为证。
翻开史书,你也许会发现,嚼槟榔过去在海南岛是很普遍的现象,家里采摘了好槟榔,主人往往要邀人前来品尝一两颗,有一首诗记述了那种令人神往的场景:
妾家溪口小回塘,茅屋藤扉蛎粉墙。
记取榕荫最深处,闲时过来吃槟榔。
需要提示一下,海南岛上居民嚼食的槟榔,与湖南湘潭人嚼食的槟榔是两码事,海南人嚼得是鲜嫩的槟榔,绿绿的,饱含水份,一颗槟榔被一分为二之后,用栳叶包着外加一点砚灰一起塞入口中。“嚼槟榔的时候要把第一口水吐掉,再吃才有味道。”在陵水,万宁,三亚街头的槟榔小摊前,老阿婆都会这样告诉一个初尝槟榔的人。其实我国的台湾岛也是嚼食鲜槟榔的大省,在那里槟榔果刚长到半个小拇指大时就被摘下来供人们嚼食。台湾人嚼槟榔也是很有讲究的,为了保鲜都要冷藏,嚼食时还得配有很好的香料,有人嚼食时你从一旁经过,也能闻到缕缕清香。
当台湾岛上的槟榔供不应求时,做槟榔生意的商人也会千里迢迢来到海南补货。台湾商人对于海南槟榔园主的要求也颇高,规定一公斤得多少颗粒,不能大不能小,有点像选“贡果”一样。
让我们回到湘潭烟熏槟榔的话题。
当嚼槟榔的习俗在湘潭慢慢形成以后,槟榔即成为人们结交朋友,出门办事不能缺少的东西,简直成了见面礼。不但大人爱嚼,就连五六岁的小孩也爱嚼,所以很多年以前,湘潭街边的孩子玩《抬轿子》的游戏时,都会边玩边唱:”轿咕轿,叽咕叽,大码头,唱人戏,吃槟榔,算我的,数毫子,算你的。”(数毫子:土话,掏钱)
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人家嫁女讨媳妇,更是买来大量的槟榔款待客人,连闹新房时也少不了“抬槟榔”的节目,喜欢闹的人会要求新郎新娘用筷子,每人夹起槟榔的一头敬献给客人。如果槟榔夹稳了,没有落在地上,客人则会说上一段祝福语:“槟榔翘起像条船,今晚花好月又圆,郎撑篙来女掌舵,百年和合好姻缘。”在闹洞房的人群中也不时有人起哄,想多赏得几口槟榔,年长的则会说:“看你讲的话戴不戴爱相,戴爱相则会多给你几口。”这时人堆中有人高声应答:“新娘槟榔两头翘,一片两片我不要,三片四片不为多,我要五子来登科”在大家的笑声中新娘会一连赏五片槟榔给那个乖巧嘴甜的人。
在湘潭周边农村,逢年过节,或谁家大屋落成,后生中举,都会去找戏班子请一台戏到村里来“擂”。人们爱听的是花鼓戏,名角演到高潮时,掌声雷动时也会有人向台上扔槟榔,以表示戏看得过瘾。清人所作《潭州竹枝记》中,对那种盛况有精彩的描述:
风流妙剧话情扬,艳姿娇容雅擅长。
一串珠喉歌婉转,有人台下掷槟榔。
总之,在湘潭只要有众人相聚的时候,管它是红喜事还是白喜事,都少不了槟榔,特别是大伙围在一堆撮一顿的时候,更是少不了将槟榔扔到桌上来助兴,槟榔在手,谁都回谈笑风生。不但享了口福,湘潭人嚼槟榔还嚼出了想象力,因切开的两片槟榔形状像“元宝”,两头翘起中间凹下,人们还赋予了槟榔“财宝”的象征意义。故旧时过大年,串门走户给亲友打拱手送“恭喜”时,主人都会给客人敬上一口槟榔,一双手接过槟榔的动作称作“采宝”,敬槟榔的人和受槟榔的人都沾到了喜气,也算是借槟榔表达新年的祝福。
“文革”前,湘潭街旁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小的槟榔店,一般是由老太太坐守,那种老式的石灰槟榔按品级放置在一排排很清洁的青瓷碟子当中,以防落灰,都有一块透明的玻璃盖在碟上,碟子下面则压着一小条价格标签,上面写着:一分钱两口,一分钱一口或二分钱一口。二分钱一口的则属“极品”了;另外,也有一分钱一小堆为细伢子准备的槟榔边子。你可以先目测槟榔上的纹路是深或浅,粗或细,纹路细而深证明是树上结的早期果,肉嫩汁多,如果你示意要买几片,老太太则会从一个竹筒里抽出一双筷子递给你,接着再将一张老黄纸铺在玻璃柜上,这样你就可以任凭经验挑肥拣瘦一番了。
后来”运动”多了起来,搞阶级斗争还忙不过来,发展地方经济就谈不上了。特别是到了“文革”年代,湘潭街头的槟榔店铺很多都不声不响关上了门。那个年代,女的烫个“波浪式”,嚼几片口香糖,都会被红卫兵几把大刷子画成漫画张贴出来,嚼槟榔也就有了风险。虽然极左人士有“宁让人吃草,不让红旗倒”的口号,但“此草非彼草”,何况上层有令,让人人都“绷紧阶级斗争那根弦”,那阵子,槟榔见得不多了,谁也担当不起“松了弦”的指责。
1978年改革开放,有了“白猫黑猫”搞活经济的政策,湘潭的槟榔生意才有了新的气象,休闲消费的概念又回到了老百姓中间,嚼槟榔又普遍起来,槟榔店更是三步一间五步一个。见湘潭本地竞争激烈,也有湘潭人舍近求远将槟榔店开到了湘潭之外的城市,单凭店前那块”正宗湘潭槟榔”的匾牌,就可招来盈门的顾客。
省会长沙的人不甘示弱,也发明了长沙特色的槟榔。说“长沙特色”主要是指制作方法有其特色,卖槟榔的大户人家中,清一色的腌制槟榔的大坛子有时多达一两百。店铺中显眼之处也常常摆放了三两个,以暗示顾客,有祖传配方深藏其中。
一方麻雀吃一方食,湘潭人是制作槟榔的老手,长沙人还没得到真传,他们怎么也做不出湘潭人那种醉人的槟榔;醉人的槟榔,能使人咀嚼时冒汗的槟榔,普遍被认为是上乘之品。对于嚼槟榔的老客而言,似醉非醉,飘飘欲仙的感觉,就是他们想要进入的状态罢了。
1995年前后,湘潭槟榔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全省许多中小城市,包括农村乡镇的人都来到湘潭进货。湘潭大桥下的大同世界一带出现了“槟榔一条街”。店铺名称以“爷”命名的为多,诸如:“老爷”、“大老爷”、“太爷”、“王爷”、“嚼爷”、“财爷”、“发爷”,还有如“王中王”、“大哥大”、“宾之郎”、“豪爵”,“花篮”等等。湘潭火红的槟榔产业带动了相关产业,如包装、香精香料、广告、运输、旅馆等等,一时湘潭市内的槟榔店铺如雨后春笋,达到了上千家,从业人员数万之众,解决了许多人的温饱。
槟榔产品的外观内质一直在与时俱进,几年下来,原来手工作坊的槟榔加工工具中部分已被省力、高效的半自动化机器所替代。现在到大一点的工厂去参观,你会见到一排排的槟榔切果机,真空包装机,还能见到蒸汽高压发仔罐,一次能发制槟榔几千斤;为防止他人造假,一般都配置了先进的进口喷码机,这种设备让众多的造假者望“洋”兴叹,只能改行或“待业”了。
1996年是湘潭槟榔初成大气的一年,也是在那时,海南岛扩大了槟榔的种植面积。到目前为止,全岛株数在三四万至八九万的槟榔园有几百个之多。条件最好的槟榔园起先都是大型国营农场,后来由私人承包。园内一排排的槟榔树整齐有序,树与树之间还安了自动淋水喷头。条件差一点的槟榔园则建在坡地上,但也土法上马挖掘了灌溉槽。
在种植槟榔树苗时,园主一般先给树苗打底肥,底肥常常是农家肥,树苗长大后再使用化肥。据行家透露,使用农家肥多的树,果实的味道就是好,纤维柔软并且多汁。槟榔树苗种下后,需要五六年的栽培才开始挂果,树龄10–25年是优良结果期,每株数年产量30至50斤不等。
在湘潭人看来,烟熏槟榔味道的好坏与熏制槟榔技师的水平有关,熏得好才出味。槟榔鲜果从树上摘下来之后,有人按其品质,大小进行分类,然后运至从事槟榔熏制的专业户那里。槟榔被熏烤之前,得先煮10至20分钟,容器是大型铁桶,高温煮后槟榔的纤维软化许多。晾干后,由技师将槟榔堆放在网状的熏制炉上,然后点火熏制。那种炉子一般长2米,宽1米,规模大的加工户有500至600个熏制炉。所用木柴多为橡胶树。无疑,熏制槟榔给槟榔产地的空气质量造成损害,岛上的空气本来清新得可以“罐装出口”。滚滚黑烟之下有人开始抗议,权衡利弊之后,当地政府提出一个建议,在远离城镇的荒凉之地开辟一个地方,用于熏烤槟榔。可是,有一些人不愿意离开家园,在环保人士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声中,他们想出另一种烤制槟榔的方法,即在烤制炉上安置一块钢板,改用煤火烤制,这就是“青果槟榔”的来历。
虽然槟榔树的种植面积在年年扩大,但嚼槟榔的人数也在同步增长,嚼槟榔的地方已由湘潭,长沙,株洲三市扩大到湖南省内所有的城镇。另外,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打工的几百万湖南籍民工也在将这种嚼槟榔的习惯传给周围的人,广东已率先跨入“槟榔大省”,湖北,江西,浙江等省也很“给力”。目前,除台湾之外,全国各省份都有人在做代理,经销湘潭槟榔。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湘潭槟榔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原来只流行于湘潭一带,今天已是全省花开,香飘临省。湖南土话中,如果说某人、某事没有特色,不精彩,人们说“出不得湖”,意思是成不了气候,走不出湖南。今天,湘潭槟榔不但走出了湖南,而且走得越来越远,甚至还回到了槟榔的原产地海南。湘琼两地的槟榔情缘是一段说不完的佳话,小槟榔写就了大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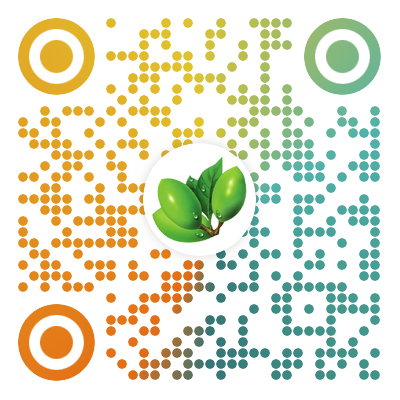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