嚼槟榔是广东悠久而重要的传统,在民国时期仍曾兴盛过一阵。招勉之《广州的抽喝吃》(《贡献》1928年第3期)说:“吃喝的中间儿,用得着牙签去刺刺,吃后仍然似刺而非刺地含在嘴巴里面,直到无意中才放弃过去。临了,向例有槟榔以殿其后,因此赏给伙计们的小钱,亦名曰槟水。近来或者因为某种空气紧张的缘故,革新得很快,槟榔已不如北京的豆蔻通行了,伙计也不向客人讨小钱。”不过槟水的称呼仍保留着,“槟水例多加一就算了事”。)
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在《东方杂志》1926年第4期写了一篇《啖槟榔的风俗》,谈他家乡海丰一带啖槟榔的风俗,说在他们那儿“差不多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食品之一”。这立即引发不少人的热情,纷纷给他写信或投稿,提供岭南各地啖槟榔的风俗例证。
清水的《关于啖槟榔的风俗之二》(《民俗周刊》1928年第13-14期合刊)也说到:“我在广州的时候,到酒楼上去喝酒时,在食餐之后,伙伴们每每送上一磕用油或火锅炸过的槟榔来,一角一角,如笔尖般大的放在磕上,赤黑赤黑的略带有白路。取带啖时,清香带苦,倒足解积滞。是以啖槟榔的风俗,我以为在广州还是很盛行的。”又说到他的故乡翁源“在十多年前,啖槟榔的风俗,还是很盛,以前更不用说。大约那时设席待客,不论官民,槟榔是少不得的。”而其《由歌谣见出广东人啖槟榔的风俗》(《民俗周刊》1928年第17-18期合刊)则说到广州、肇庆等地的除夕均有“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槟榔”的歌谣。
民国民俗歌谣中与槟榔有关的恋爱婚姻歌谣,向来是少人关注的。《民俗周刊》1928年23-24期清水的《再谈啖槟榔的风俗》:“广东人喜欢啖槟榔,已成为很古很古的风俗,是以有许多美丽的、和谐的歌谣,都在歌咏槟榔。”较早的爱情民歌见于明徐火勃的《徐氏笔精》卷五,“蛮歌”云:“老龙山下有狂风,老龙山上月朦胧。槟榔劝郎郎不醉,辜负奴唇一点红。”此后这类美丽的民歌便层出不穷。如湖北孝感夏力恕《菜香根舍诗草》卷一二《掇南粤风景为竹枝词》:“一炉金鸭女儿香,万手蒲葵玳瑁光。咀嚼不须临案食,绕庭红雨是槟榔。”李调元的《南海竹枝词十六首》有:“见客纤纤指甲红,一方洋帕献槟榔。”(《石泉书屋诗钞》卷一)
范端的《粤中见闻》有:“槟榔白,不食花;食花蒂,当灵茶。槟榔青,子初成;食青子,当茶青。”隐隐地可作情歌。顺德梁启鋆的《羊城竹枝词》,则是标准的情歌了:“钅及槟枨触破瓜思,细裹青蒌嚼欲痴。染得桃唇红似血,教郎错认是胭脂。”“真情两处合芬芳,妾是叶兮郎是榔。仁核在心深意会,陈朱结后送槟香。”麦其镳的《羊城竹枝词》更是:“扶留叶绿槟榔香,龙女低声递马郎。郎似宾门叶似妾,结成一对好鸳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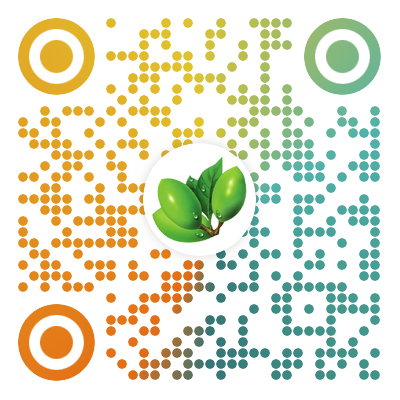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