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椰子树是男人树;槟榔树是女人树。”二十几年前我头一回去海南岛,就听说了这么句话。
椰子树,枝干简洁高大,油绿的叶子巨扇般宽阔舒朗,海风吹过椰子林,犹如万千旌旗哗啦啦招展,威风八面,尽显男儿气魄。就连椰子果也着实像个好男人,外壳坚硬,掷地有声,内心里包容着一片澄澈的海。
槟榔树,挺拔俊秀,修长的腰身微微彰显着曲线美,树干节节灰白犹如罗裙裹身,顶端露出一节青嫩的酥胸,树冠处簇生着凤尾般的翠叶,那是她婆娑摇曳的秀发。槟榔的果子看上去娇小可人,嚼起来脸红心跳,热汗涔涔间让人微生醉意,很有那么点风韵女郎的味道。“高高的树上结槟榔,谁先爬上谁先尝……”暧昧的歌词,赋予人美妙的想象。
当地人介绍说,在海南满眼的椰子林并不稀罕,但槟榔树却象征着财富。你要是远远望见椰海中有一丛槟榔树,那树下必有一户人家。槟榔树越多表明那户人家越殷实,嫁姑娘时也必会备上一份好嫁妆。因为槟榔子嚼起来生津解渴不说,而且又辛又甘,提神又爽,是当地人放不下的癖好。尽管槟榔嚼久了会让人嘴唇猩红,牙齿漆黑,可据说在早年间,当地的姑娘正是以红唇黑齿为美的。
嚼槟榔透着神秘,很多远来的游客也想尝尝。不过一旦看见到路边地上的滩滩血红,并被告知那并非血迹,而是嚼槟榔后吐出来的汁水时,很多人难免望而却步。脚下令人恐怖的槟榔印记怎么也和眼前俏丽的槟榔树联系不起来。也有好奇者经不住诱惑斗胆一试。接过抹着熟石灰的青蒌叶子包裹的一颗嫩绿的槟榔子,一口下去,刹那间口腔里像是开启了翻滚过天车,咽喉顿时被噎住。这第一口,太浓烈,受不了,只好要吐掉。是所谓“先吐赤水一口,而后啖其余汁。”难怪当初苏东坡老先生来到海南嚼过槟榔之后留下了这样的诗句:“北客初未谙,劝食俗难阻。中虚畏泄气,始嚼或半吐。吸津得微甘,著齿随亦苦。面目太严冷,滋味绝媚妩。”
嚼槟榔的习俗古已有之,甚至那染红的朱唇也变成了香艳的诗。“锈床斜依娇无那,烂嚼红葺,笑向檀郎唾。”有人认为李煜这首《一斛珠》里的“红葺”并非红绒线,而是槟榔。想来也是,嚼着槟榔心醉神迷飘飘欲仙,个中滋味要比绒线更来得勾魂蚀骨。
槟榔的嚼法花样很多,用蒌叶、石灰搭配着新鲜槟榔子算是一大类。海南、台湾等槟榔产地大多如此,而且把那颗鲜嫩的槟榔子叫做菁仔。石灰可以是贝壳烧制后研磨成粉,也可以用大理石煅烧水洗加工成白灰,还可以加入姜黄或中药材变成略带甘甜的红灰。槟榔强酸性,石灰强碱性,咀嚼时牙齿每摩擦一次就发生一次激烈的化学反应,涌现出千变滋味和那一口殷红的汁水。
把槟榔蒸煮熟了,或干燥或盐腌或蜜饯制干货,再嚼起来依然会脸面潮红精神焕发,但却不至于染个血盆大口。像盐水槟榔涩里带咸,上面挂着层盐霜;糊槟榔又焦又脆,一咬就碎;用冰糖蒸过的枣儿槟榔棕润殷红,如甘如饴。早年间老北京的烟儿铺里还有卖烟熏槟榔的。《红楼梦》里有一段描写贾琏和尤二姐调情,接过尤二姐的槟榔荷包,拣了半块吃剩下的撂在口中吃了,又将剩下的都揣了起来,这里的槟榔想必就是这种干货。
嚼干槟榔的嗜好百多年前在两广、两湖、江浙、京津等地都非常流行,后来逐渐被吸烟草所取得。现在这一遗风尚存的恐怕只有湖南了。其他地方的人,大多觉得那是遥远的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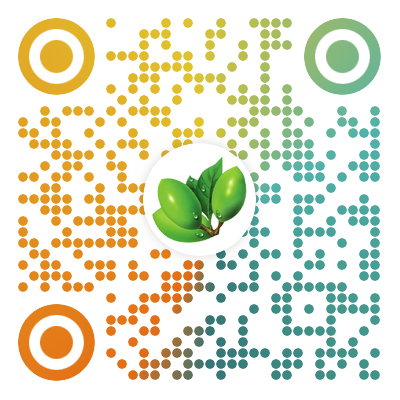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